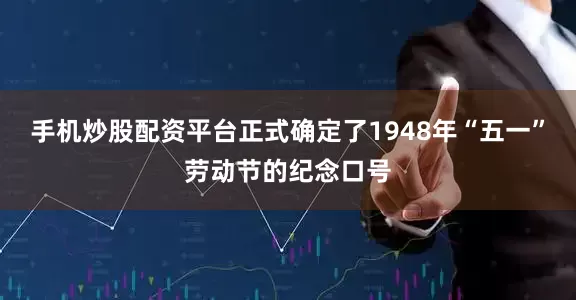
父亲邓拓
邓拓与毛泽东(上)
邓小虹
1944年五月,父亲主持编纂并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该著作被誉为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首部《毛泽东选集》。其广泛流传,深远影响,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1949年至1958年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担任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与社长一职。期间,他屡遭毛泽东同志的严格批评与指责,最终,他选择了主动辞去报社职务,转而投身于北京市委的工作。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毛泽东的伴侣江青,联合姚文元、戚本禹等一众御用文士,对我父亲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反党黑帮集团的首恶”、“叛徒”等多重罪名。他的著作《燕山夜话》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遭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猛烈抨击。这些无端的指控,几乎将我父亲推向了绝境。
后人难以揣摩,那位父亲与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何纠葛?为何他会从毛的赞颂者沦为笔锋下的牺牲者?
一
首版《毛泽东选集》出版
在毛泽东思想早期宣传的关键阶段,我的父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938年四月,父亲正值26岁盛年,被委以重任,担任《抗敌报》的主任一职。该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自此,他投身于晋察冀边区长达十年的宣传舆论战线上。《晋察冀日报》社不仅是一家报社,同时也是出版社,更是新华书店的分店。在其出版的众多书刊中,马克思主义著作占据了显著的比例。
昔日,周明叔曾任《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他回忆道:
1938年“七一”庆典过后数日,邓拓手捧《解放》杂志踏入工厂,他言道:《论持久战》一经发表,便显露出毛主席深邃的智慧!其文辞之精妙,论证之有力,逻辑之严密,无一不体现着辩证法的精髓,实乃指导抗日战争的宝贵理论武器。我们报社不仅要发行报纸,更要肩负出书、创办出版社的重任。值此抗战一周年之际,我们便以“七七出版社”的名称,先行印制此书,以期边区的干部和民众能够迅速阅读。
这标志着《晋察冀日报》出版的首部著作,亦为邓拓在抗战初期伊始,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初始力作。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父亲凭借参与革命的长久经历,对毛泽东同志卓越的指挥艺术与非凡的文采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因此,在个人学习和工作期间,他养成了深入研究与搜集毛泽东同志著作稿件的习惯。据周明回忆,在他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人员时,邓拓曾特意提醒他,要求将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研究这些著作的书籍,都送至他处。此外,他还特别关注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亲笔手迹。
1948年四月,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任弼时同志抵达阜平县城的南庄。自毛泽东同志交付《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文章起,每篇稿件在打印出清样后,都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进行最后的校对。邓拓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审定的清样尤为珍视,悉数收藏。
1942年四月,晋察冀日报社精心策划并编撰了《毛泽东言论选集》,其中收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篇章,为《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44年1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布指示,强调在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党内外应广泛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为此,决定编纂并出版《毛泽东选集》,父亲受命担任主编。肩负重任的父亲,依托晋察冀日报社所存资料,自年初便开始着手编辑工作。历经四个月的辛勤努力,至四月,资料搜集、文稿筛选工作圆满完成,并提交分局审批。令人赞叹的是,仅用了短短一个月,选集便在五月顺利印刷出版。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他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刻理解和熟稔。

1944年,《晋察冀日报》出版。
《毛泽东选集》主编:邓拓
父亲在毛选印刷时对周明说:《毛泽东选集》的文稿业已整理完毕,其中所选文章均经过分局严格审核,并已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予以批准。此外,我还曾计划增选数篇文章,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该文尚未公开面世,故此次未能纳入选集。
父亲在撰写这部《毛选》的“编者的话”时,巧妙地引入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术语,满怀热忱地对其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对其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扮演的卓越角色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继五卷本问世后,《毛泽东选集》于1945年和1947年分别经历了两次修订与再版。1947年的增订使得内容增至38篇文章,篇幅达到60万字,从而扩充至六卷。我父所编的《毛泽东选集》在解放前得以广泛翻印,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各地解放区。到了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更被译成俄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并传播至海外。
历经半个世纪,直至1999年11月27日,《长江日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湖北襄樊出土的珍贵资料——一套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在这部选集中,毛泽东曾论述过“引进外资”的观点。当周明叔叔,时年已84岁,阅读了这篇报道后,他亲笔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一方面主要依赖中国人民自身积累,另一方面则借助外部援助。只要外国投资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持开放态度欢迎之。”
有利于中国人民及外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中国在实现了稳定的国内与国际和平,完成了全面的政治和土地改革之后,方能生机勃勃地推动轻重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外国投资的接纳空间极为广阔。一个政治上倒退、经济上贫困的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极为不利,对外国人民亦是如此。
这段论述揭示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明确提出,应积极引进外资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即便是在现今广泛流传的四卷本著作中,也未能找到这一重要观点的详细记载。
周明叔叔说:
《毛选》四卷本的问世,既经过了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审订,亦凝聚了诸多文士的心血。当时删去的那一段,固然可以理解,鉴于抗美援朝的背景。然而,我们接纳前苏联的援助,本质上也是一种引进外资的行为,这些内容理应保留。至于第六卷本的编定,更是由你的父亲倾注心血最终完成的。
二
父亲深爱毛泽东。
1936年二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即将抵达陕北。毛主席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词作。《沁园春 雪》:
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远眺长城蜿蜒于内外,只见苍茫一片;俯瞰大河横贯上下游,顿时波涛不再汹涌。
山峦起伏,银蛇飞舞,原野奔驰的蜡象,似乎正欲与天公一较高下。
晴日赏红装,分外妖娆。
江山娇,英雄折腰。
秦皇汉武,文采略逊;唐宗宋祖,风骚稍逊。
一代英豪,成吉思汗,唯有弯弓射雕之技。
往者数风流,今朝看。
字里行间洋溢着无与伦比的雄伟气概和满腔的喜悦与欢愉!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展开和平协商之际,应柳亚子之请,便将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重新誊写,赠予柳亚子。柳亚子阅读后,赞叹不已,赞誉毛泽东为“词坛第一人”,认为即便是苏轼、辛弃疾也难以匹敌,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于是,他邀请亲朋好友共同品鉴。最终,重庆的《新民晚报》甚至全文刊登了这首词。
毛泽东的这首词一经公开发表,即刻在山城引起了轰动,举世瞩目。
蒋介石览过此词,愤懑与忧虑交织于心。他紧急告知部属,“我看毛泽东心怀勃勃野心,意图称帝称王,崇尚复古,企图倒退。尔等速速组织一批人手,撰写文章,以批驳其言行。”
随即,国民党向各地及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号召擅长吟诗作词的党员以诗词形式,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较高下。身处重庆的郭沫若、远在延安的黄齐生、山东解放区的陈毅等人,纷纷挥毫泼墨,为毛主席的词作献上自己的词章,加入了这场论战。由此,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两大阵营、两派文人间的笔墨较量。
当时,我父亲身处晋察冀解放区,亦积极投身其中,他的身影活跃在革命的第一线。沁园春·步毛主席原韵是这样写的:
北斗悬南,真理显明,旗帜飘扬。
正义之师遍布四方,邪气消散无踪;战鼓声声,众人同心协力,意志如潮。
故国辉煌,长矛在手,谁敢轻言魔道胜于正道?
从头记,谁指点此奇娆?
血雨红娇,笑尽忠贤屈腰。
羽檄频传,引得豪情满怀;号角齐鸣,驱散了心头的慌乱!
策略超群,巧思独运,愿将江山重塑新颜!
此后,观人间盛景,岁岁朝朝。
四十余年后,一位来自宝岛的政论家谈及此事,仍不禁扼腕叹息:“遗憾的是,国民党的队伍虽庞大,然而其中充斥的不过是擅长抓捕、拘禁、处决、攫取私利的特务与贪官,以及那些只会撰写空洞无物的党八股的迂腐儒生与酸丁级别的奴才文官、学者。直至他们逃离大陆之际,国民党竟然一首《沁园春》式的佳作也未能够创作出来。”
1948年四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们从陕北启程,抵达了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彼时,《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正坐落在城南庄附近的新房子村,距离不过两里之遥。一日清晨,中央局打来紧急电话,要求父亲即刻前往参加一场重要会议。父亲抵达城南庄后,有幸首次与一直敬仰的毛主席见面,两人热情握手,毛主席显得尤为高兴,并与父亲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4月30日,在城南庄,党中央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1948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口号。在此期间,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已暂停发行,而《晋察冀日报》则承担起直接传达中央意志的重任。当年,该报社的编委陈春森叔叔回忆道:
中央明确要求“五一口号”务必在5月1日当天的报纸上刊登。那日,我担任值班编辑,鉴于任务之重要性,邓拓亦亲临编辑室与我共同值守。夜幕低垂,10点稍过,毛主席亲自审定的稿件终于送达。我们注意到,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段,系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于原稿之上。事不宜迟,邓拓与我不待片刻,即刻着手编排,并将稿件迅速送往印刷厂进行排字、校对及印刷工作。
5月1日,《晋察冀日报》首次刊发了“五一口号”,该口号一经新华广播电台播送,即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便是以“五一口号”作为其最早提出的主张。
《晋察冀日报》曾公开发表“五一口号”,如今这份报纸在城南庄纪念馆的显眼位置展出,使得城南庄成为了人民政协创意精神的圣域。父亲对这份承载着毛泽东亲笔字迹的珍贵手稿格外珍视,他叮嘱我,一旦排版完成,便立刻将手稿交到他手中。

1948年,《晋察冀日报》首次刊载了“五一口号”。
父亲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对毛的诗词、文章尤为钟爱,更对其书法情有独钟。我们幼时便目睹了他将那些毛主席亲笔批示过的社论文章一一保存,并精心装帧成册,视作无上珍宝。在他书房的案头,常年挂着一幅荣宝斋精心制作的1949年毛主席手录唐代少年诗人王勃作品的木版水印书法;而父亲本人的书法作品中,抄录毛主席的诗词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或许,正是由于上一代革命者对毛主席在建党、建国时期展现的理论见解与卓越才能深感崇敬与赞誉,将他推上了无上的神龛,使得他逐渐沉溺其中。建国之后,他身为国家领袖,为消除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剔除党内外的不和谐因素,借助自身的威望与权力,屡次发起政治运动,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三
因为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
1949年春,伴随着党中央及华北局领导机构的进驻,首都北平,《人民日报》亦踏入这片新土。2月2日,作为北平市委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宣告诞生,首期发行量达五万份,迅速被一抢而空。在创刊号上,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宣传部长邓拓亲自执笔的代发刊词得以刊发。奋斗建设民主北平。
同年八月,中央作出决策,将《人民日报》升级为中共中央直接主管的机关报。此举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的胡乔木同志负责,他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一职。
张磐石晚年忆述:踏入北平后,《人民日报》总体表现尚佳,大体上履行了中央机关报的职责。然而,在引导和阐释各民主党派的声音、文艺界的观点以及国际舆论方面,显得力量不足。加之个人健康状况不佳,加之不擅于撰写言论文章,这成为《人民日报》言论相对薄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廖承志,当时负责新华社工作,曾私下与他进行交流,告知他中央有意将邓拓调至《人民日报》任职。廖承志说:邓拓文采斐然,学识渊博。他虽带有几分书卷气,但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更能施展其才华。
1949年10月,父亲肩负重任,重返《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回到了他钟爱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在这十年间,由《晋察冀日报》培养的一批优秀骨干人才,已纷纷投身于新中国各省机关报的骨干岗位,而他却毅然决然地不带任何旧部,独自一人走上新的征程。
甫一履新,他便彰显了一位从沙场历练而来的党报领导者的气魄:首先,他着手在各地区建立记者站,并培育起一支通讯员队伍,使得《人民日报》的通讯员人数从原先的数百人激增至万人以上。伴随着遍布各地的通讯网络逐步建立,我国新闻传播的全国格局得以迅速拓展;其次,他强调每日必须发表社论,以此确立党报的核心精神和支柱。
昔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胡绩伟曾对吾弟邓壮言道:“那时众人都知晓邓拓在党内享有盛誉,然而他的真才实学却鲜为人知。撰写社论,我们皆感力不从心,听闻他执笔如风,笔走龙蛇,便恳请他亲自动笔,为我们示范几篇佳作。此举虽是存心考验您父亲,甚至玩笑般地给予他一丝压力,但终究未能难倒他。”
1949年,报纸每月发表的社论平均不足八篇。然而,到了1952年,全年发表的社论数量激增至208篇,其中父亲亲自执笔撰写了19篇。与此同时,报纸的总发行量亦呈现显著增长,从1949年底的9万份增至1952年的48万份,并在1953年进一步攀升至55万份。胡绩伟曾言,彼时,《人民日报》的同事们齐心协力,全力以赴,致力于将报纸办得更加出色。《人民日报》的众多同仁普遍认为,这段时期堪称该报历史上最为令人怀恋的、充满活力的繁荣时期。
建国初期,文坛上爆发了三大争议事件: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的批判以及胡风事件。在这场文化风波中,《人民日报》身处风口浪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挥了关键作用,却在这三大文化冤案中扮演了令人不齿的角色。
同时,我国正面临如何构建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争论。父亲身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自然而然地被卷入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之中,时常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
在上海《文汇报》的某篇《“阳谋”——1957》的述文中,主编徐铸成回忆起父亲曾与他进行的一次对话,当时父亲言道:偶尔,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念头,渴望辞去在《人民日报》的工作,转而投身于另一份报纸的编辑行列。
1956年发生的一件事,父亲直接触怒了毛泽东。
1955年,我国农村迎来合作化运动的鼎盛时期;次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浪潮在北京率先掀起,随后迅速席卷全国。面对这种急躁冒进的态势,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深感忧虑,担忧其中可能隐藏的隐患。同年6月,刘少奇亲自部署,要求中宣部草拟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文中写道:急躁冒进之所以演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乃是因为它并非仅限于基层干部之中,更严重的是,它首先在各个系统的领导层中显现。许多基层的急躁冒进行为,实乃上层压力所催生。社论进而深入剖析了急躁情绪滋生之思想根源,明确指出——“此现象主要源于我们在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因此,在各项工作中,无论其紧急程度或重要与否,亦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可行性,均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企图一蹴而就,期望在短短的一日之内便完成所有事务。”
这乃是我国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反对“左”倾错误的社论。此篇佳作一经问世,便如重磅炸弹般震撼文坛。父亲在审阅稿件后稍作润色,便精心排版成清样,呈送至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手中。他们均亲笔修订,细致打磨,终将清样呈至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审阅后,仅以三个字定夺。“不看了”。(毛后来说:“骂我的不看。””说明他还是看了!)
在这三个字中,父亲敏锐地察觉到毛泽东并不认同社论所持的观点。若不发布,刘少奇与周恩来总理那边将难以解释;若发布,毛泽东又不会满意。这让父亲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特意在定稿上注明“全文明日见报,改为新五号字体”,意图通过缩小字体来降低其关注度。
6月20日,社论如期发布。然而,伴随“路线斗争”的加剧,社论所倡导的正当理念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其所批判的急躁冒进风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愈演愈烈。
这篇社论给父亲带来巨大的不幸,以后为此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攻一点,不涉及其他。。他说:“1956年,我国在经济文化领域实现了显著的飞跃,然而,部分同志对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却过分强调不足,甚至将进步视为冒进,一时间,一股非议之风席卷而来,导致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纲要四十条以及促进会等措施被否定,这对今年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让民众感受到了寒意。”会上,毛批评了父。
四
《人民日报》改版,毛不满意。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强调必须调动党内与党外、国内与国外所有积极力量,致力于将我国塑造为一位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紧接着,5月和6月间,刘少奇连续三次发布指示,着重强调新闻宣传的改进,旨在提升我国新闻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国内的经济及民主建设进程。
为落实党的指导方针,确保《人民日报》与人民群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更加生动地展现社会风貌,使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手段,父亲动员报社全体同仁深入自查工作,并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报纸的宝贵意见。编委会经过严谨研讨,向党中央提交了改进工作的专项报告。党中央予以批准,并同意了《人民日报》编委会提出的改进工作计划。
秉承中央的明确指示,自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由原先的四个版面扩充至八个版面。这不仅意味着篇幅增加了一倍,更标志着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当日的社论明确指出:《人民日报》既是党的喉舌,更是人民的喉舌,“我们之所以将报纸命名为‘人民日报’,意在强调它乃人民所共有、共用的武器与财富。人民,才是报纸真正的主人。正因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我们方能将这份报纸办得更加出色”。
经改版后的报纸,汲取了民国时期办报的智慧,增设了副刊版块,并邀请了诸多名家撰写杂文与散文。该报在拓宽报道领域、倡导自由讨论以及优化文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革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胡绩伟回忆道,人民日报的全面革新,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翻开了一页崭新的历史篇章。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那些经过改革焕然一新的报纸,将化身为我国新闻宝藏中的瑰宝。在那个时期,《人民日报》的同事们团结一心,倾尽全力以提升报纸质量,许多同志都深情地认为,这段时光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让人铭记的繁荣昌盛时期。
竟未料想,在改版之后,毛召集乔木及其父亲一同前来,言道:“是谁准许你们进行改版的?当前纸张资源紧张,却频繁增版,这哪里是读者能全部消化的?既然改成这样,那么从今往后,我不再阅读人民日报了!”
胡乔木被迫开口。“主席,关于《人民日报》的改版事宜,我已向您进行了汇报并征得了您的同意,随后邓拓等人方才着手进行改版工作。”
这时毛说:“我言辞恳切,然而你们却置若罔闻。即便我只需轻描淡写地放个屁,你们却立刻遵从。”
尽管党中央已正式批准了这场大改版,然而毛本人却并未表示赞同。当试刊样本呈送至他面前时,他的态度并不满意。对报社同仁们倾注心血所进行的重大改版提出的批评,使得人民日报的领导层深感失望。
广盛网配资-10大配资公司-配资论坛是什么-炒股杠杆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